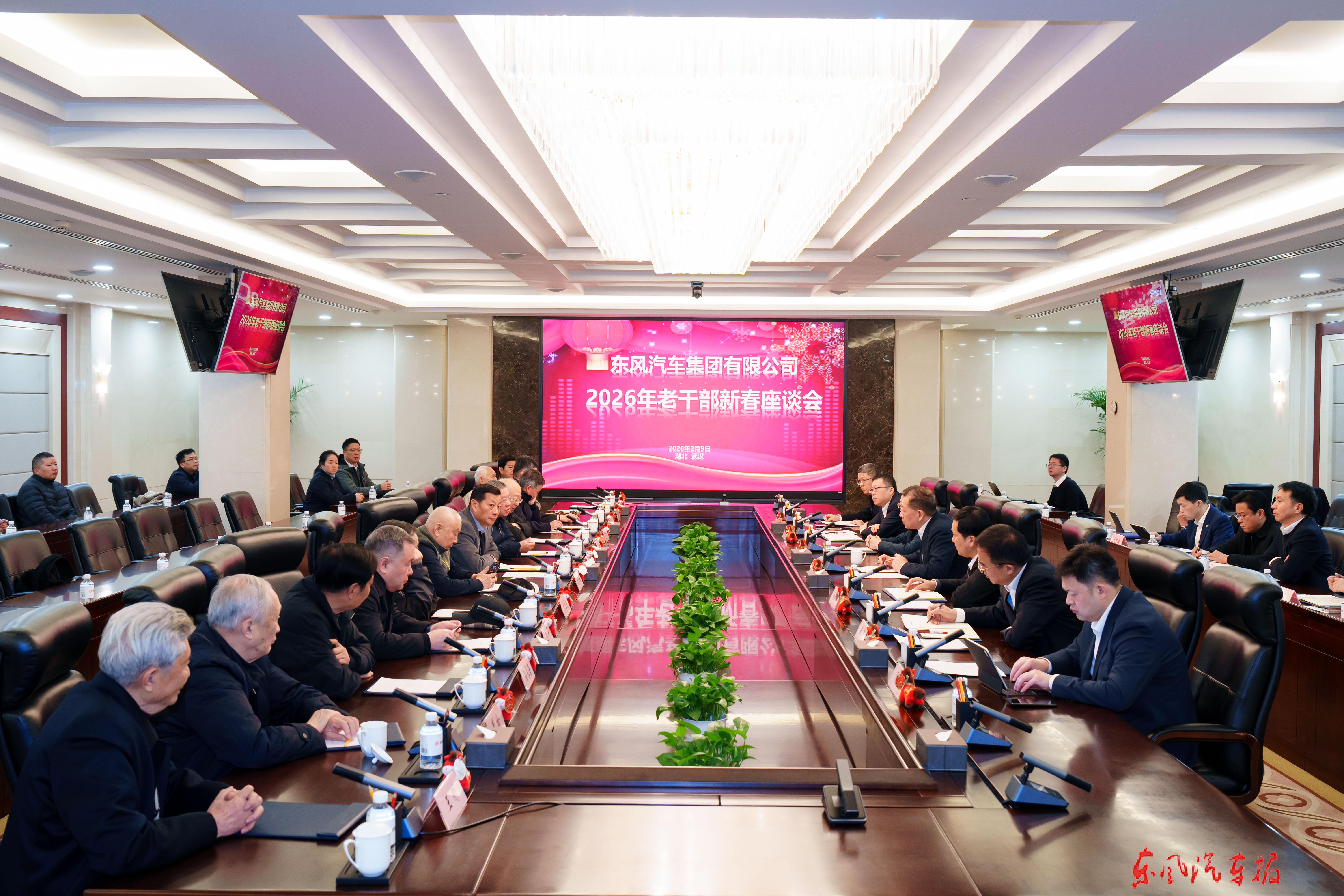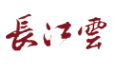父亲总爱站在阳台抽烟,烟头明明灭灭间,常对着远处的稻田叹气:"当年那九千块,够买一套房呢。"他说的是八九十年代两件扎心的事,像两枚生锈的图钉,永远钉在记忆的墙面上。
“农转非申请下来了,咱们家有三个指标呢”1987年的夏天特别热,父亲兴奋地举着几张表回到家里,妈妈拿过盖着公章的表单,细细地摩娑着,禁不住擦拭着眼角的泪水,喜极而泣。要知道,那时节"农转非"是响当当的金字招牌,村里的赤脚医生转了户口,就能去镇医院吃商品粮;小学老师转了户口,每月多拿二十块补贴。父亲算过账:他在单位每月挣327块,转三个人的户口要攒足三年工资。但母亲总说"孩子以后能在城里吃上商品粮",于是全家咬碎后槽牙,凑齐九千多块,换来了三页盖着红戳的户籍证明。
那些年父亲的自行车铃铛格外响,车把上总别着户口本,仿佛揣着金銮殿的圣旨。可谁能料到,这转到城市户口作用还没发挥,到了二十一世纪,村里开始分宅基地,表弟的农村户口能批三分地盖小楼;前几年土地确权,邻村的发小靠承包田拿分红,父亲却只能对着泛黄的户口本叹气,说:"当年要是不转户口,也能在村子盖房子了。"语气里混着烟灰的苦味。
另一桩遗憾藏在客厅的老衣柜里。那是台红色的电话机,塑料壳上还留着父亲当年用红漆描的"吉祥如意"。1994年我家所有的小区开始装电话,那时候装电话要交1280元初装费,相当于父亲四个月的工资。装机那天,父亲特意请了一天假,买了一个红色的电话机,我们一家一直守在装电话的师傅旁,等线路接通了,父亲拿起姑姑的电话号码,把第一个电话打给姑姑。可听筒里传来的是"嘟——嘟——"的忙音,原来没有提前与姑姑沟通好,正好家里没人,开通电话的第一天硬是没有电话可打。电话安装后,父亲有空就守在旁边,默默地抽着烟,只要电话铃响一声,他就立刻放下报纸,咳嗽着接起:"喂?喂!"多数时候是打错的,偶尔是串线的电流声,反倒是我常偷用电话给同学打长途,被父亲发现时,话费单上的数字能让他的烟蒂在地上烫出焦黑的印记。
那些所谓的遗憾,其实是一代人用血汗写下的时代注脚。父亲的九千块和一千块,买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是在浪潮中站稳脚跟的渴望。如今户口本上的"非农业"早已泛黄,电话机的转盘也转不动了,但那些在岁月里辗转的焦虑与期待,终究沉淀成我们理解父辈的密码。就像父亲总说的:"遗憾归遗憾,可当年要是不这么选,谁知道会不会有更大的遗憾呢?"暮色里,他的背影与阳台上的老电话机重叠,仿佛在与时光轻轻和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