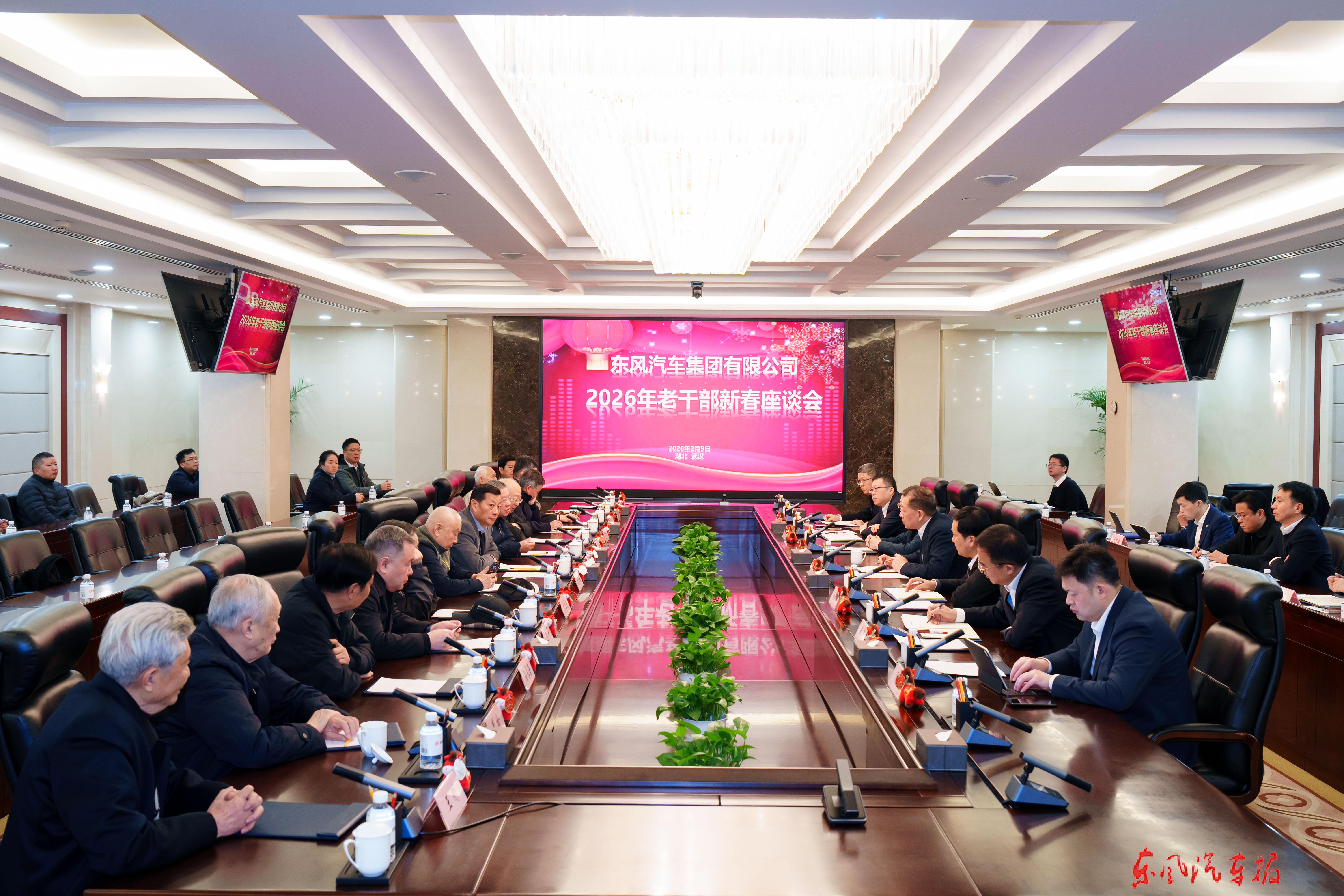这两天刷到重庆姑娘呆呆的刨猪汤视频时,屏幕里的热闹几乎要溢出屏幕。这个担心老父亲按不住年猪的姑娘,一句“请你吃刨猪汤”的求助,竟引来数千网友驱车赴约,车队从村头排到村尾,素不相识的人自发分工按猪、烧火、做菜,深夜的庭院里烟火升腾,铁锅翻滚着乳白的浓汤,那股子纯粹的热闹,瞬间勾起了我对童年杀年猪的记忆。
小时候,杀年猪是农村腊月里最隆重的仪式。进了冬月,父亲就会翻黄历选红煞白 ,提前将日子定下来,然后再通知村里杀猪的好把式王伯,顺带挨家挨户招呼邻里:“后天杀年猪,过来搭把手,顺便请大家吃刨猪汤!”虽然那时候大家都还不很富裕,平常很少有荤腥类 ,也就是过年才能吃上一碗杀猪菜,但全村老少无论谁家杀年猪,都会邀请左邻右舍前去捧场作客。杀年猪的前一晚,母亲会把堂屋清扫干净,在神龛下点燃三支香,念叨着告知祖先,语气里满是对丰收的敬畏。我和哥哥则揣着兴奋睡不着,满脑子都是即将到来的热闹和喷香的杀猪菜。
天刚蒙蒙亮,灶上的大铁锅便冒起了白蒙蒙的水汽,空气里有一种沉稳而幸福的等待。随着王伯一声令下,男人们扛着梯子、拎着麻绳赶来,有的去猪圈牵猪,有的在空地上搭挂架,王伯早已摆好尖刀、刨子和接血盆,神情干练。“一二三,使劲!” 几声吆喝里,四个壮汉合力将肥硕的年猪抬上案板,那时的我总被母亲牢牢挡在身后,只敢从指缝里偷看那惊心动魄的一幕 :父亲按住猪身,王伯手持尖刀精准下刀……孩童的心分不清是害怕还是激动,只记得那声响彻山谷的嚎叫声过后,一切又趋于平静。接着便是热火朝天的协作:烧沸水、刮猪毛、开肠破肚……母亲早已在盆里撒了盐,不停搅拌防止凝固。猪毛褪去后,雪白的猪身被挂钩吊起,剖开的瞬间,那便是冬日里最解馋的杀猪菜。
院子的另一角,女人们的战场同样热闹。奶奶和婶娘们围在柴火灶旁,洗菜、切肉、灌血肠,案板上摆满了张家刚从地里拔的白菜,李家现挖的萝卜,王家腌的酸菜。“今年这猪养得好,油脂足!” 二婶一边煸炒五花肉,一边笑着说,锅里的油花滋滋作响,香气很快弥漫了整个庭院。我最爱蹲在灶边添柴,看火苗舔舐铁锅,看母亲把猪血、猪肝、粉肠依次下锅,乳白色的汤汁翻滚着,撒上一把蒜苗,鲜味儿直钻鼻腔。
晌午时分,八仙桌在院子里摆了好几张,爸爸被推到了主客位,邻里乡亲围坐一堂。红烧肉色泽红亮,肥而不腻;酸菜炒猪肝脆嫩入味;最受欢迎的还是那锅刨猪汤,舀一勺喝下去,鲜醇绵长,浑身都暖透了。炊烟袅袅裹着肉香飘满了整个村子,大锅里酸菜咕咚冒泡,血肠在沸水里慢慢鼓胀 大人们端着粗瓷碗,聊着今年的收成和明年的打算,笑声此起彼伏;孩子们捧着碗穿梭在桌椅间,比谁碗里的肉更多。王伯喝了口酒,慢悠悠地说:“一家杀猪,全村帮忙,这才叫过年!” 此刻,没有陌生与隔阂,只有热气腾腾的烟火气和流淌在席间的情。
如今生活好了,吃肉早已不是稀罕事,超市的猪肉已被分割的精细标准,我们便捷的获得食物,似乎弄掉了那份等待、劳作、分享所带来的扎实的喜悦与温情。小时候杀年猪,杀的是丰收的喜悦,吃的是地道的鲜香,更是邻里间无需言说的默契与真诚。你帮我按猪,我为你添柴,一碗刨猪汤里,盛着最朴素的乡情,藏着最温暖的人心。
原来,我们怀念的从来不是某一种味道,而是味道里裹挟的情谊,是传统里流淌的温暖,是再也回不去却永远铭记的旧时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