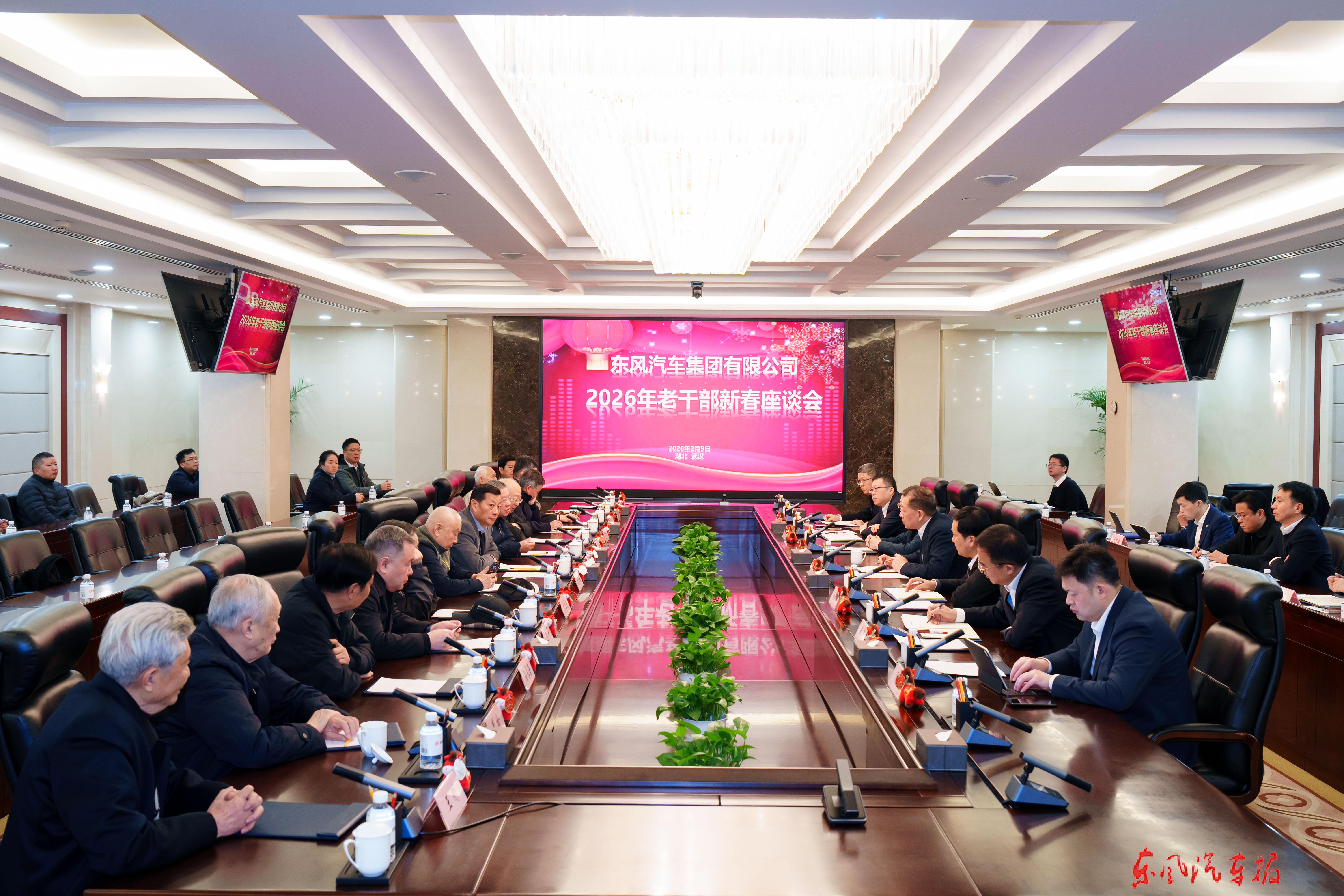如今 跪在一个小土堆前
我们就隔着一块矮小的石碑
如今 我仍习惯从上衣口袋
掏出一粒石子
它来自沙漠 温润沉默
如同你极简的一生
话不多 静静地
在羊群后面
放下滚烫的沙漠余温
回家
停电的油灯下
少不了再翻一翻发黄的字典
学会写三代人的名字
以及“羊”“一群羊”
长夜里 透过粗糙的手
光影里追问
那飞鸟的叫法
它从泥墙上
飞出 时而振翅 时而轻盈
听 羊群倒膜 蝙蝠和猫头鹰
披上夜衣出发
羊奶焙上 黑柴根烧得噼里啪啦
新的一天还很长
有那么一次
无意再触到这小石粒
恰如洗脚碰到你的踝骨
一盆水足够勾勒一个人的行踪
走过雪地 或
蹲在沙坳点上烟锅
偶尔 撩起羊皮袄挡风打火
几声沉重的咳嗽
风雪里 谁都不知道
是惊起的沙云雀
还是你的帽子在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