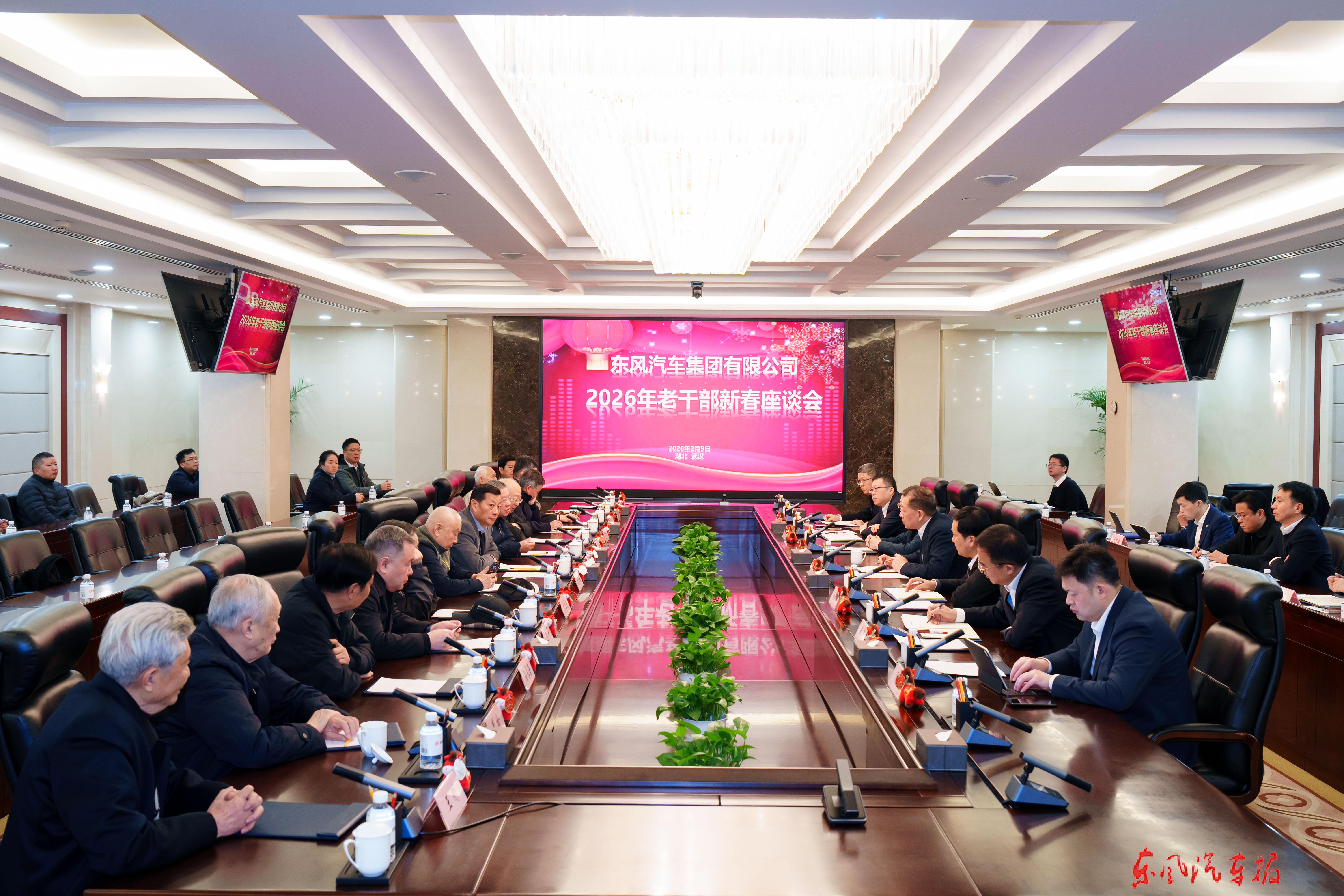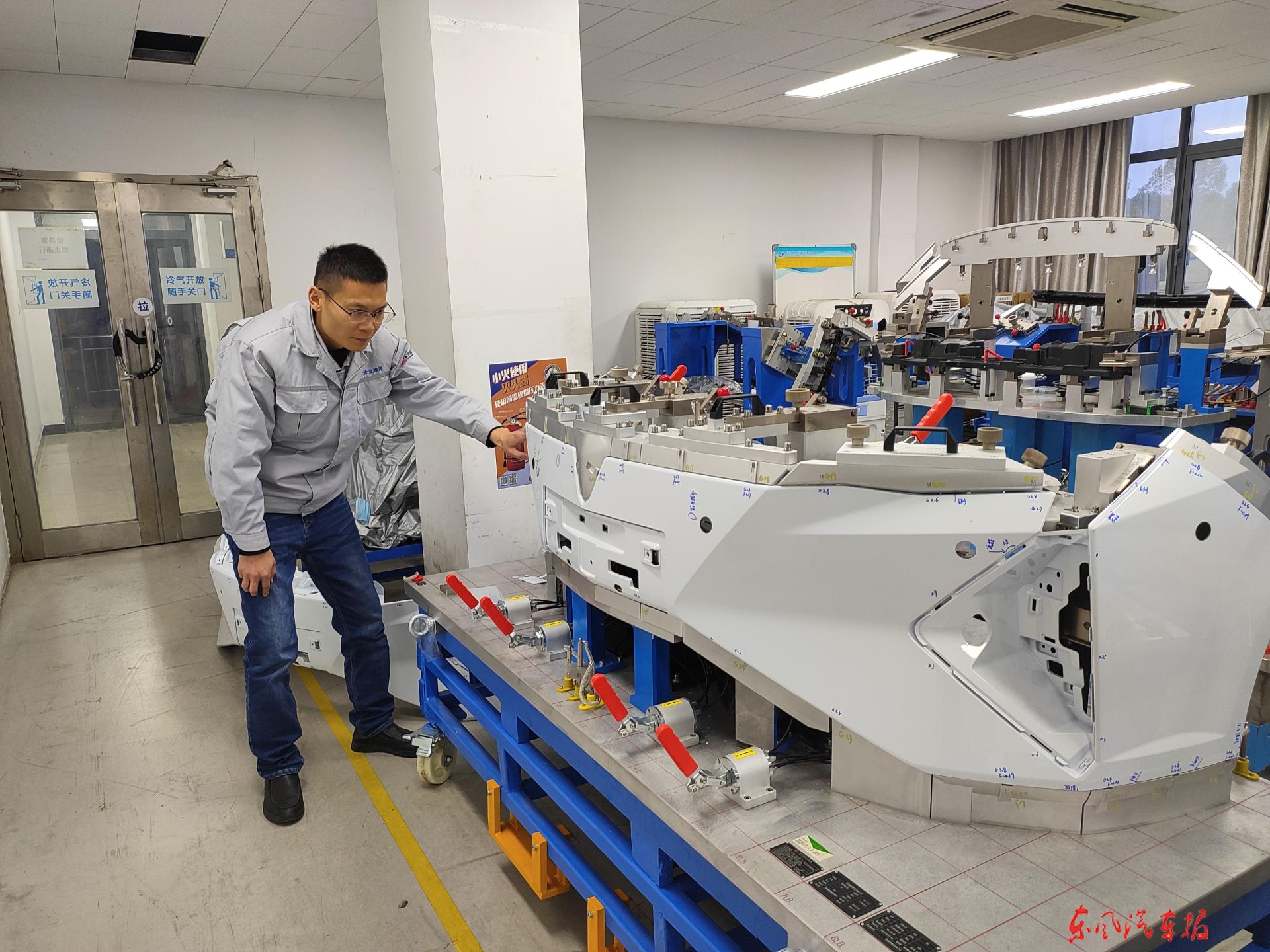和妻子领取结婚证后,妻子所在单位分了一套30平米左右的房子。这对于从中学起就一直住集体宿舍的我来说,是一个新的纪元!
那是一幢建厂初期的楼房,共三层楼高,建筑风格是典型的T字形,中间楼梯,左右是走廊。按学历和工龄排序,我们分到的是第三层的把头,和其他户型比,我们多出了阳台过道的那部分面积。
拿到钥匙后,我和妻子就开始忙碌起来,把之前住户搬家余下的物品悉数清除,托熟人找施工队将屋子刷白。说是施工队,其实干活的就是一个小伙子。那些天,下了班我就到房子里,看小伙子一招一式地刮灰打磨,眼见房子一天一天的变化,内心的喜悦难以言表。
闲谈中得知小伙子是郧西人,在十堰跟着师傅做了几年临工,慢慢一个人开始独立干,师傅按天给工钱。一开始小伙子还很腼腆,不怎么和我们说话,但干活很认真,不惜力地刮灰打磨,跟个雪人似的,我们心生感激,每次过去都会给他带点水果,小伙子很不安,连连推辞,在我们的一再坚持下,才接了过去,小心地放在墙角,用报纸遮住,干起活来更加细致。
可能是为了消除一个人干活的寂寞,也可能是为了驱散疲劳,小伙子带了个放音机,循环往复地放流行歌曲,边听边用带着厚重口音的嗓门和着放音机唱,那样子十分陶醉,歌声与飘散的石灰,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弥漫。
再后来,我了解到,小伙子姓兰,因家庭条件不好,中学没读完不得已辍学到城里打工,挣钱供弟弟妹妹上学和贴补家用。言语中,我听出了他对现实的无奈,也看出他对我的羡慕,心里好生庆幸。
半个月后,房子的工期几近结束,小伙子要转到其他工地干活。临走的头一天傍晚,我请他在马路边的摊上吃了餐饭,几乎不喝酒的我破例要了两瓶啤酒。小伙子很动情,说我们是他遇到的最好的“雇主”,和我们的交往,让他体会到了这个城市的温暖……临分手时,我发觉小伙子的眼圈红了,我也一样。
不久后,我们住进了那间屋子,开启了和妻子的新生活。虽是陋室,我却很珍惜,为了提高房子使用效率,闲暇时就喜欢收拾屋子,这里装个挂钩,那里搭个支架,而我的点滴改善也每每得到妻子的肯定和鼓励,由此也激发了我更大的热情,这种热情一直延续到现在。
在这里,我们迎来了儿子的出生,霎时屋子变得更加拥挤,等到儿子开始学走路了,每天我都会将地面擦拭得一尘不染,看儿子在屋子里伴着学步车横冲直撞或在地面滚爬撒欢的样子,心里快乐无比!
后来,我几次和妻子散步到小伙子告诉过我的住处(61厂铁路道口旁边的一个临时工棚)找他,可每次都是铁将军把门,那之后,再也没有遇见过小伙子了,但他哼的《九儿》的调儿,常常在我耳畔萦绕。
很多年后,每次开车回十堰,下了高速,路过那个铁道口,我都不由自主地将视线投向我内心以为是的那个地方……
在小屋住了大概3年,我们搬家到了另外一个地方,离开小屋前,我们将小屋收拾得干干净净,依依不舍地和小屋告别,至今,小屋留给我的记忆,始终无法忘却。
我时常想,这个我连名字都不知道的打工仔就是我人生中的一个过客,但他于我的意义,是让我第一次深切地感受到了“家”对于我的意义——温暖、归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