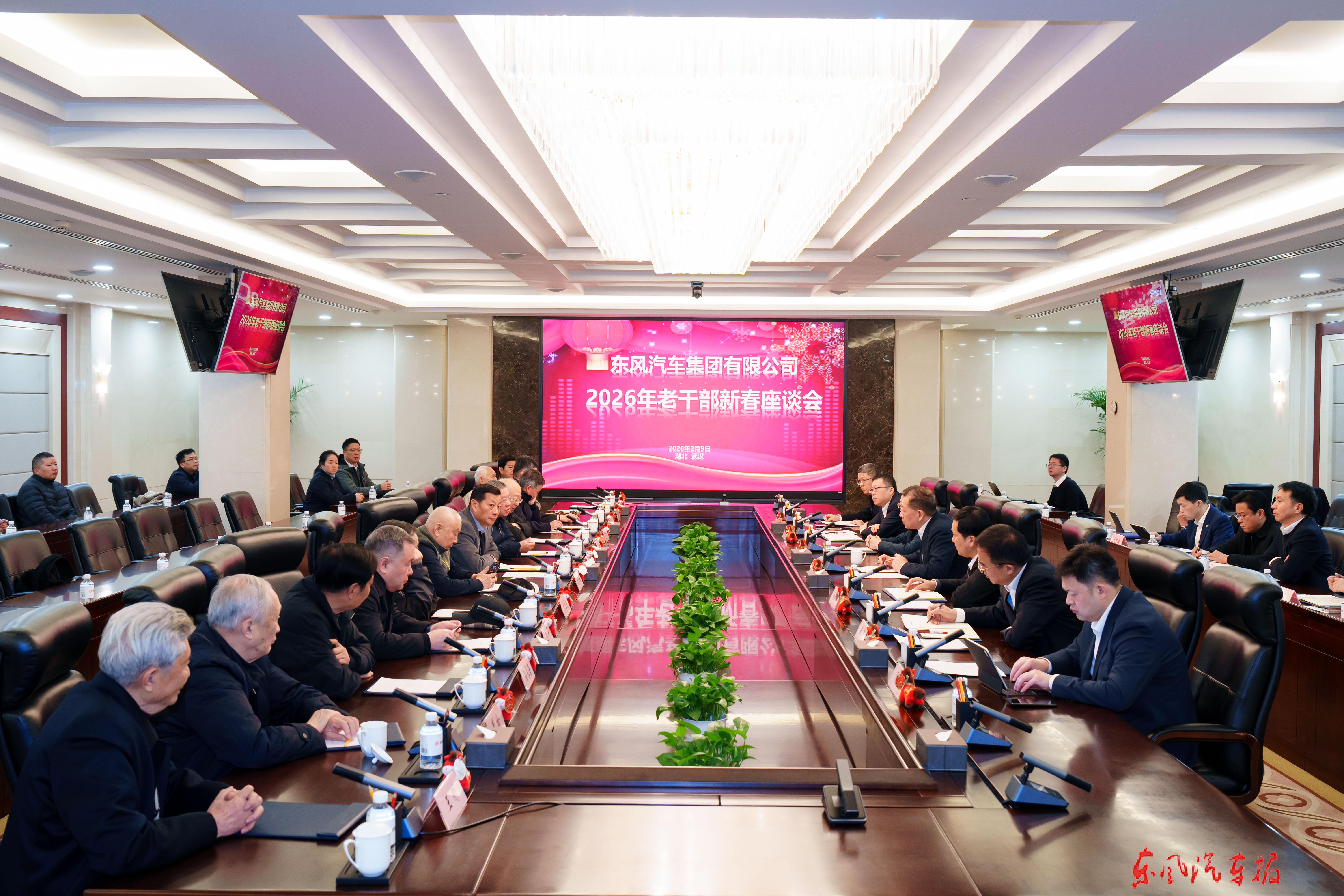缺少泥土的都市生活,日渐钝化着城里人对季节递变的感觉。然而,每至开镰时节,高楼里的我,总能隐隐听到声声布谷,自老家的田野,穿越山山水水,飘进城市……
随着侵袭而来的谷香,恍惚中,我赤脚站在了老家湿漉漉的田埂上。
老家在江汉平原的东北边缘,介于平原、山地的过渡地带,曾经青山秀水,山冈、溪流、森林、鸟鸣声中含着别样风情。
桃花流水鳜鱼肥。这时节,老家的农事正旺,田野里,青苔笠,绿蓑衣,斜风细雨中,老家人守望着清气氤氲的泥土,泥土里生长着老家人迷离的梦。
四月,夕阳山外山,妍黄的油菜花镶嵌在绿油油的麦海之间,远远地看,宛如铺天盖地的七彩毯。坡腰上的牛,悠然地啃着草,老家就成了幅浓墨重彩的工笔画了。
到六月,澎湃的麦黄,满川满坡地滚淌;金黄的海洋里,疏散的村庄仿佛一座座时隐时现的绿岛;老家浸淫在不可抗拒的麦香里。明月下,小院里便响起霍霍的磨镰声。黎明时,老家人要去田地里,收割热烈的夏天。这些汗水、喜悦一起流淌的日子,老家到处都是醉人的镰舂麦的沙沙声。娃子们,迎着朝霞,踩着野草清馨的田埂,紧随着“粒粒归仓”走过六月。金黄过后,明镜样的田畴里,又被老家人灵动的手,插上一行行诗一般的秧苗,稚嫩的诗句倾诉着老家人的又一个期盼。
“双抢”后的老家,小河畔杨柳烟,浣衣村姑互逗笑,惊乍一片水鸟。林子里,醉里嬉语相媚好,而最喜童稚无赖,塘口卧剥莲蓬,好一派乐陶陶的农家景致。
十里稻花香。秋渐渐地走来,日日地成熟。待到熟透时,老家人便将它收获,堆放在谷场上。谷场便没日没夜地沸腾起来。笑歌声里轻雷动,一夜连枷到天明。秋收中,老家人积蓄起来的欢乐要把稻场撑破似的。你看看,累了,老家人就坐在待扬尘的金色谷粒上,神仙似的抽锅旱烟,要么喝一口刚汲取的井水,要么远远地与人扯上几句;饿了,竹篮里有新面摊馍,陶罐盛着粥。最快活的是村娃子们,或上树摘果,或满村子撒欢,或在飘溢着香气的稻草堆里“躲猫儿”。
岁月深处的老家,鲜花盛开,于我总是那么的生动、丰韵和美丽。
日暮乡关何处是,烟波江上使人愁。
我知道,不可回避的,随着父母辞世,老家距我愈来愈远了。
然而,老家记载着往日抹不去的欢乐、苦难、泪水、笑语、质朴;它是泥土情结的凝聚,有着经久不息母亲一样的厚爱,有着父亲一般的若谷襟怀;是在外受伤的人梦归的没有风浪的港湾,是走出老家的人最初也是最终的驿站。
尤其爱听《故乡情》:他乡也有情,他乡也有爱,我却常在梦里故乡行!
于是,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有“金窝、银窝,舍不得自家草窝”之说,为什么从古至今有“叶落归根”之说,为什么有“月是故乡明”“乡音未改鬓毛衰”之叹,为什么思乡之愁才下眉头、却上心头,为什么走遍天涯海角而回家的打算时时在心口。是啊,老家是走出老家人的根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