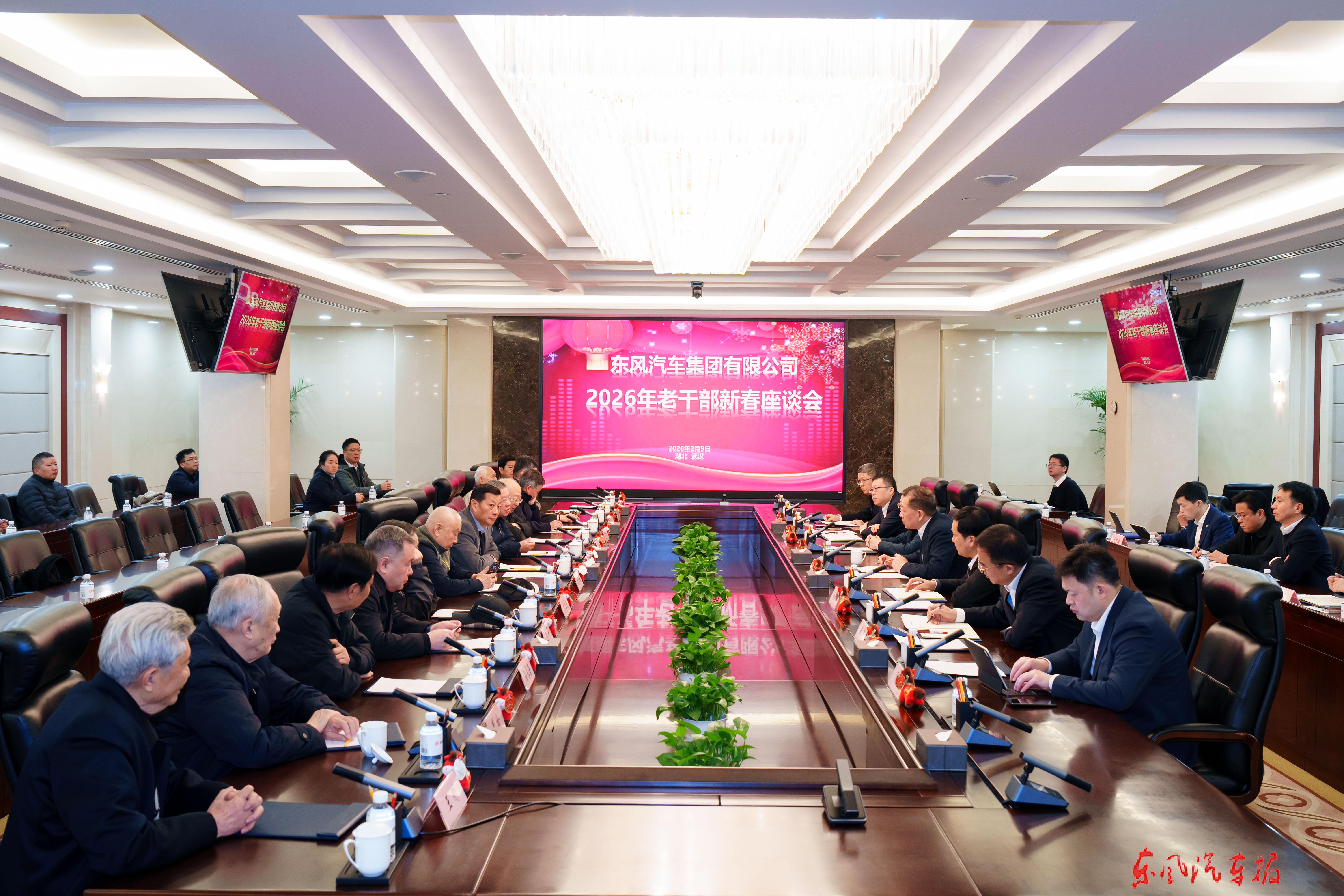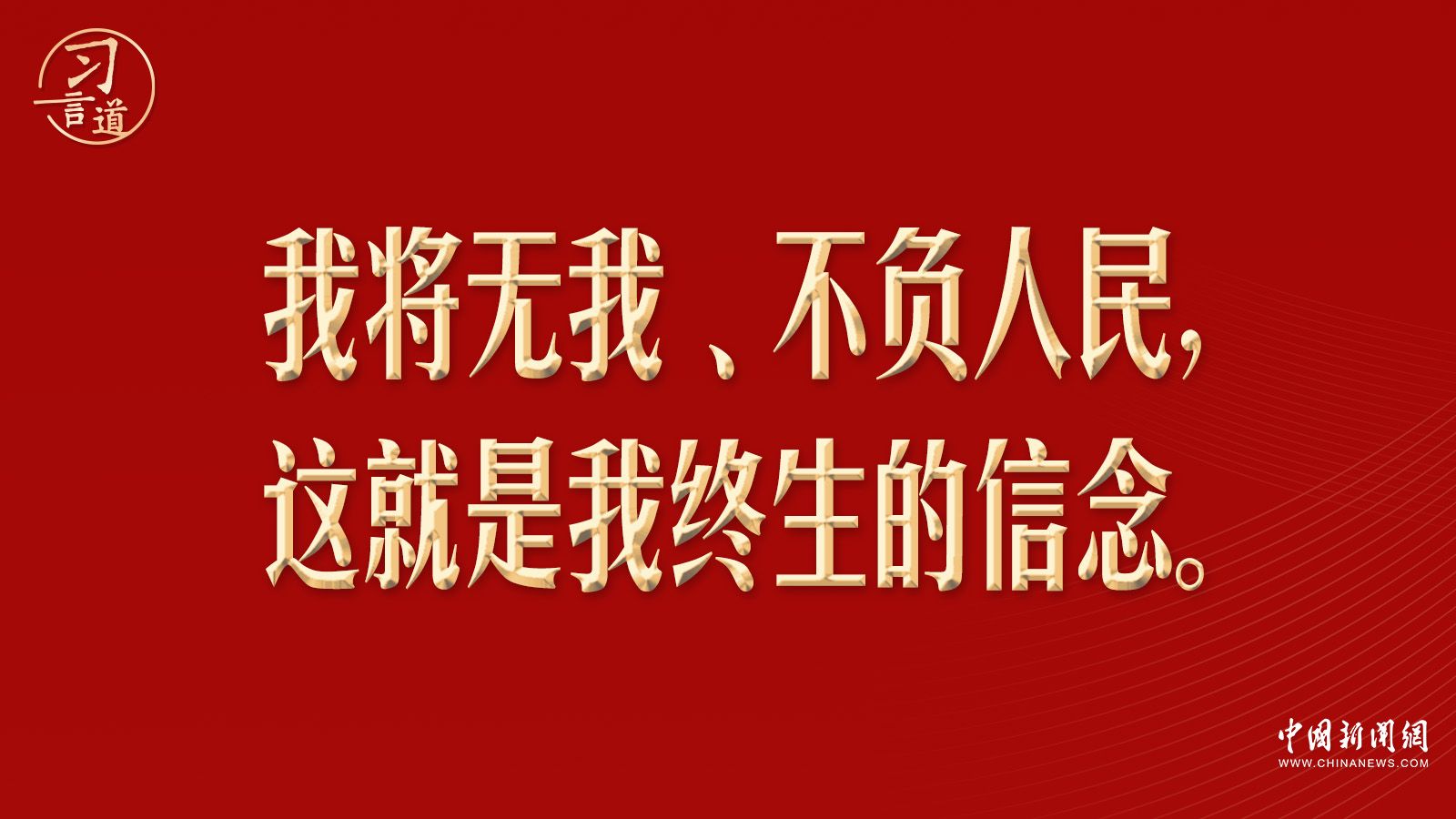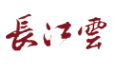江汉平原上的很多地方,原先都是以种两季水稻为主,主要是当时的水稻产量有限,就希望在不多的田地里多收点粮食。于是,在春秋之间的那个火热的夏季,“双抢”成为我们最关注的抢收早稻、抢种晚稻。
长江边的天气,不仅仅是热,还很湿,所以热起来也更让人难受些。早晨太阳刚刚露出头,就已经很有火气了。而地里的早稻正等着收割。挥舞的镰刀拨动稻杆,那些稻穗倒也有不少的香气,只是热气也很让人还能忍受。如果收割持续到下午,连稻田里的水都很烫脚和腿的,稻秆摆动,就是铺面而来的热浪。活儿累是一方面,更主要是热得累人!
收割完了,还得靠人力把稻子挑回家跟前的打谷场上,在那样高到39°气温的情况下,身上的汗出的非常多,就象刚从河里爬上来一样的。
这时候,需要兵分两路,一路去把收割完的稻田整出来。翻地、耙地、平地,直到把满是稻杆茬的地整成一片“白水”,看不到什么东西,为插秧作准备;一路则把收割回来的稻子铺在打谷场上,用石头碾子把谷子碾下来叫“脱粒”,拉碾子的动力是拖拉机或者水牛。
在这些事的间隙里,就需要去秧苗地里,把秧苗拔起来,洗尽泥巴,挑到整好的稻田里。
收过早稻的地里,水已经被太阳烤得可以。很多的鱼象泥鳅和鳝鱼,就被热昏了,而被我们专门在午后收获!
收割稻子是拿着镰刀向前,而插秧则是左手拿秧苗,右手分插地向后倒退。腰都是弯的厉害。看着前面还有很远的稻浪,或者后面还有好长的“白水”,都是不敢直起腰来,天气热,还是快点干完为好啊。终于一畦到头了,很有些成就感;当全部的一块地都结束后,腰也累的直不起来了。这时候最希望的是把自己放倒在一个阴凉的地方,把腰好好地来个“矫枉过正”。
刚从大集体变成包产到户时,人们是男女老少齐上阵,都担心误了时节,所以更是累的够呛。晚上还趁着凉一点儿时,牵着牛脱粒。累了一天,实在是没神,有时,牵着牛,转着圈,人都可以睡着了!
好像90年代末期,人们大多不搞双抢了一是杂交水稻的产量大大提高,可以顶早稻和晚稻两季加起来的水平,二是双抢实在是太累了,在那么热的天气里,人的效率也发挥不了,倒是经常中暑。
其实,一块地种两季,由于生长期偏短,所产的水稻还真不如一季的杂交水稻好吃。
南方人总是吃米饭,像农村里的人,只有夏天才吃三顿,也是三顿米饭,面食很少。但在大集体时,每年的双抢结束后,都会有个类似于会餐的事。就是由生产队统一买很多的油条、包子、炸肉饼等,都是平时几乎不吃的、也没钱吃的面食,然后按照每户挣的工分的多少分发到各户。真的是一件让我们孩子们解馋的大事了!
在农事告一段落的夜晚,家家户户都把脱粒过的稻草铺到路面和路边,而我们小孩就会带着床单,拿着大蒲扇,三五成群地聚到那些路边上。把床单铺在厚厚的稻草上,躺上去,看着偶尔的满天的星星,闻着稻杆的一股清香,说些家长里短的闲话,一会儿就在那里入梦了。
稻子满仓的时候,家里人都很高兴。等到秋天的晚稻收割,更会让人看到生气勃勃和希望的增长,就像人家说“手中有粮,心中不慌”吧。
水稻交替生长的季节,那个火热的春秋之间的忙碌季节,那个既播种希望、又收获满仓的季节,那个令人难忘的“双抢”季节。